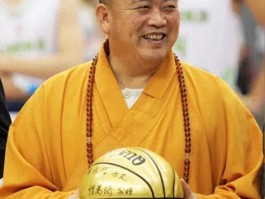见到“日本人学校”这几个字,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疑问:这些孩子为何不直接去当地学校就读,反而要另外划出一块地方,建造起一座楼宇,还要搭建一个几乎和东京教室一模一样的附属小天地?

答案藏在北京朝阳区那栋灰白小楼里。

清晨八时,校门开启,众多身着藏青色制服的学子鱼贯而入,课程安排与日本保持一致,就连午餐时供应的味增汤,也由横滨方面统一配给。
走廊贴着修学旅行照片,不是故宫,是奈良喂鹿。
教师团队多数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直接委派,其薪资待遇由日本企业联合会提供支持,外派人员的子女只需缴纳少量象征性费用即可入学。
放学后,他们能够去邻边的茶艺馆品鉴茶水,也可以进入丰田出资建立的实验室,在那里分解汽车引擎。
北京日本商工会每月会到访一次,他们带着名片盒,向初三学生讲述如何进入东京总部就职,似乎认定十年后的学生们会重返那个岛国。
抵达上海,相似的情景在虹桥和浦东各重现了一遍,只是场面更为宏大。

虹桥校区的入口有地铁2号线,来接孩子的家长大多带着行李箱,浦东校区的入口则停着公司的客车。
学校的双语课程安排得非常紧凑,上午安排了日语和数学,下午英语教师直接使用上海方言讲解牛顿的学说。
文化节期间,附近小学的孩子们也被邀请参与制作团扇,彼此间交流存在隔阂,但气氛依然欢乐。
那位教师表达得颇为中肯,意思是让两方能够互相认识,其实暗含的意思所有人都明白——日本公司的负责人每三年就会调换工作地点,他们的子女最终必定要离开,尽早促成一些联系便算是尽了份内之事。
苏州那边更干脆。
淮海路七十九号入口处看起来很普通,像是家日式餐馆,里面却别有天地:有游泳设施,有网球场,还有一条小型的樱花小径。

学校要求学生每学期参观一次日立工厂,了解空调压缩机如何由钢板转变为机械装置;然后到苏州工业园区实验小学进行一场友好的足球比赛。
孩子们回到家中动笔写作,中国的小伙伴笔下是“球传得飞快”,而日本的小朋友则记叙了“食堂里有个人在吃辣条”。
看起来很单纯,实际上却为将来的上司和伙伴设下伏笔——我认识你的面容,进行交易时得先端水,再谈条件。
广州高新园区风信路10号将科技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该校2018年才落成,校门处有两台白色机械装置主动致意,教室内摆放着乐高机器人与索尼编程工具。
七年级便着手制作APP模型,指导教师是软银的专家,研究项目旨在为广汽丰田节省百分之一的物流周期。
学生家长听完汇报,鼓掌拍得比看棒球还卖力。

大家普遍认为这门课程安排合理,因为这些人未来打算不是进入丰田的研究机构,就是返回东京从事编程工作,而广州的炎热天气,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。
相比之下,深圳南山那条工业八路就显得有人味得多。
这栋建筑的外表不如蛇口那家卖甜品的小店引人注目,不过每逢周末,四海公园里总能见到穿着制服的学生在收集空瓶,由教师引导,家人们负责提供垃圾收集袋。
参与公益服务可获得学积分,赴日升学时需提交实践记录,若篇幅不足将不予认证。
旁边的招商供电公司干脆把旧电线捐出来,让他们做环保手工展。
日本孩童初闻电线杆可作美术教材,本地居民惊见邻边国际学校师生亦会从事清扫工作,两重震撼交织成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互动。

天津双港镇的校区气候最为严寒,设施也最为扎实。那栋1998年建成的教学楼,沿用着当年的教学计划,整体没有改动,只是增添了一间航海模拟的房间。
教室里装了舵轮和雷达屏幕,初二就能考小型船舶证。
距离港口有二十分钟车程,学生们在暑假期间登上货轮前往韩国进行一次环游,返回后撰写一篇关于“集装箱内寿司温度变化情况”的报告。
老师说明情况时显得漫不经心,天津港缺少掌握日语的调度人员,需要预先对他们进行培训,目的是为了日后节省翻译开支。
话糙理不糙,算盘打得啪啪响。
观察这些校区,可以察觉到它们构成一个隐秘的快速通道系统,一头连接在华日本资企业的招聘需求,另一头则与东京总部的员工库相连,两者之间以学生作为过渡环节。

学校变成了极富温情的入职演练场,课程安排依照公司轮岗计划编排成了个人发展路线图。
国内家长们看了心生向往,展现出国际化气质,掌握两种语言,使用先进设施;而日本家长们心里十分明白,这相当于一条安全带,倘若将来孩子返回日本,他们的学业背景、人际交往以及文化适应都能顺利衔接,没有任何损失。
真正的裂痕往往潜藏在那些未曾言说的片刻:比如课间十分钟,苏州那群孩子漫步至邻近中国小学的围墙边,目睹其他孩子玩跳皮筋,因无法沟通而欲加入又不得不笑着退回;又如在深圳做义工时,一位中国老奶奶用粤语向他们表达谢意,他们误听成日语的“谢谢”,随即齐齐鞠躬,老奶奶因而惊恐地后退两步——正是这些微小的窘迫,才显露出平行宇宙间偶发的错位所留下的真切痕迹。
火花一多,保险绳也许就不那么结实了。
归根结底,这些日本学校并非某些人猜测的情报机构,也不是故事中描绘的与世隔绝的乐土,它们实际上是国际企业的支持设施,兼做文化交流的辅助工作。
一旦行业趋势发生转变,或者外派机制终止,校园或许会立刻转变为办公区域。

在那个时刻,最不愿意离开的,也许不是那些在日企担任要职的人,而是那些向中国奶奶习得第一句粤语话的孩子们。